在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中,看法国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埃德加.莫兰(Edgar Morin)的 《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》,可以说是正当其时。
此书是1999年在巴黎出版的,所思所想与我们在大疫中的感受几乎同步而高度共鸣,可见其思想的穿透力和理论的洞察力。莫兰的学术生涯,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,在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。他最重要的主张, 是面对错综复杂和日益不确定的世界,我们需要革新文明的范式,用“复杂性思维”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未来。

【法】埃德加.莫兰著,陈一壮译 《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莫兰关于不确定性的思考
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后果,在造就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巨大进步的同时,也埋下了毁坏这一文明的暗线。今天,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,每一个全球性问题——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、人口激增和贫困问题、核武器扩散和战争威胁、难民和移民潮、恐怖主义等等——无不是高度综合和复杂的。突袭全世界的新冠病毒,则是一个最新的警示: 我们征服自然和争霸世界的雄心与我们的能力是不相称的,抗疫表面上反映的问题是公共卫生危机和防疫水平、社会治理和全球合作能力等;背后却是我们的知识观、方法论、世界观,是我们认知世界的眼光出了问题。
知识系统的迟滞和失序,早已被学者觉察。1959年,英国物理学家C. P. 斯诺首先提出“两种文化”的命题,指人类文化被割裂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,两者不仅互不相通,而且互相鄙视,难以对话。莫兰其实是延续了这一讨论。60年之后,情况究竟是改善了,还是更加糟糕了?
莫兰分析了科学的范式问题。尽管人类问题日益综合并且错综复杂,已经成为跨学科的、多维度的、跨国界的、总体性和全球化的;但是自牛顿时代建立的教条仍然占统治地位,这就是以分析为主、还原论、线性因果关系、决定论等传统“科学方法”和思维范式。C.P.斯诺呼吁的是培养我们这个时代兼通文理的通才,但现实却是伴随知识激增、学科分化导致的“超级专业化”。我们“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比例过大的各个学科的专家”,但知识系统却“愈来愈脱离人类的控制”,因为科学的范式总体上仍然是分离、肢解和箱格化的,整体性的问题被“像红肠一样切割开”,成为“超级专家”的盘中餐。
莫兰称超级的学科精神变成了一种“地主精神”,仿佛用排尿来标志地盘的狼群,禁止他人的进入。无限细分的微观研究,还原论的后果之一,是掩盖了整体的复杂性、实体的多维度性、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关系等等,因而往往失去了对复杂问题的总体性和根本性认知。
莫兰还敏锐地指出了还原论的另一个特性:把研究局限于可测定、可量化、可形式化的东西上。然而,现实的生命、活动大多数是不能被数学化和形式化的。我自己的感受,量化研究的泛滥,是用各种术语、概念、算法筑起专业化的高墙,使非专家完全看不懂;而研究的结论,有些与经验高度一致,完全不需要用那么“高深”的研究;有些是明显违背常识的,其余的那些发现和分析,则是令人将信将疑的,同类研究的结果也相差很大。海德格尔称迷信数量分析的“算术狂”“吞吃了计算的本质”,嚼碎了存在、性质和复杂性,超级专家丧失了设想整体性和根本性的能力,一个显例是经济学。在最具精确性、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领域,不仅专家难以在经济预测上意见一致,其预测又常常是错误的;更不用说完全无力预测和防范如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。经济学因此成为“数学上最先进的和人文最落后的学科”。因为它拒绝面对复杂性,而是将经济活动简化再简化、定量再定量,因为它“不能思考无法量化的东西,也就是说人类的热情和需要。”哈耶克因此说“没有一个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可以成为大经济学家”;而且“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会变得有害无益,甚至构成一种真正的危险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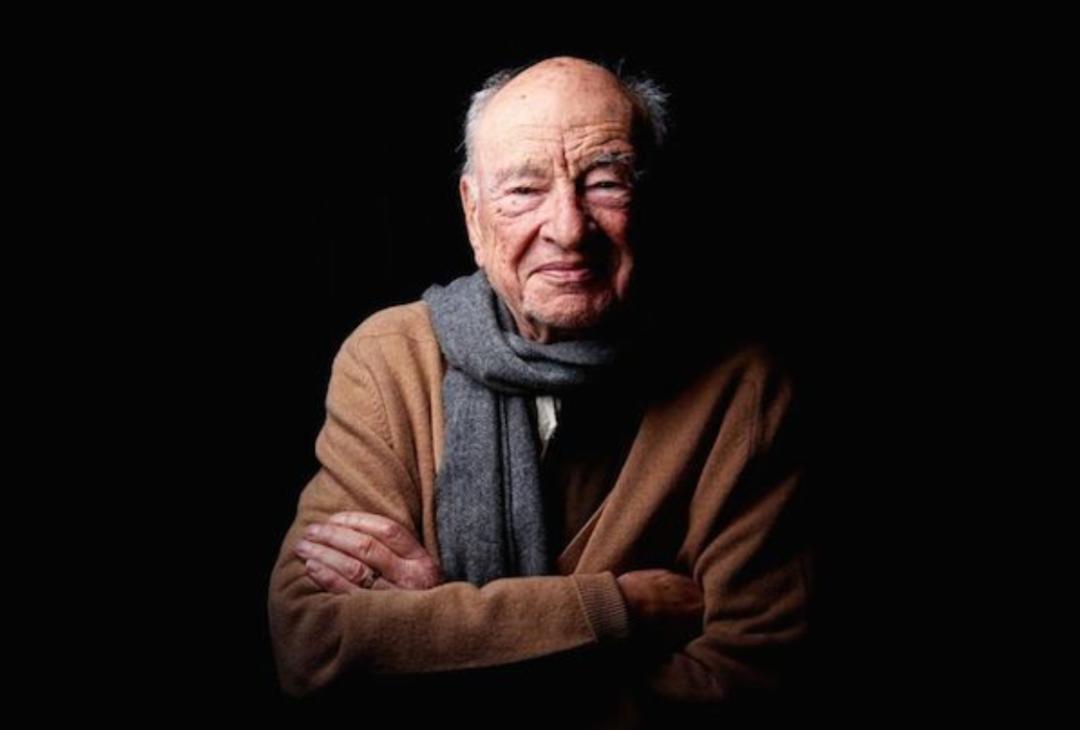
▲埃德加·莫兰
特别令人受益的,是莫兰强烈地意识到知识激增、学科割裂和超级专业化的技术-科学化进程对公民的挑战,导致民主的大幅度倒退,“民主的亏损在不断增长。”社会的“高级种姓”和“技术特权集团”把日益增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处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,对重大问题的垄断,剥夺了公民认知的权利、侵蚀了公民总体性和深度思维的能力。对当代战争的认识,可以形象地认识这种“民主的亏损”:过去我们可以利用插在地图上的小旗来跟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,那么今天对战争的电脑计算、情景模拟、远程打击等等,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了。最极端的是“原子武器完全剥夺了公民反思和控制它的可能性,”而被交由国家首领的个人决断。因此,他说,“政治愈是变成技术性的,民主的权能就愈是萎缩。”
文明范式的陈旧落后,致使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是“弱智”的。莫兰指出“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、沙俄帝国中的苏维埃革命、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、1939年德苏条约的戏剧性变化、法国的崩溃、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顽强抵抗,所有这些都是出乎意料的;直到1989年的意外事件——柏林墙的倒塌、苏维埃帝国的瓦解、南斯拉夫战争。今天我们处于黑夜和浓雾之中,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。”结论是 “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,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”,我们面临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、非线性、自发性、混沌等新特征,需要学会“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与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。” 没有历史的“规律”,没有被允诺的进步,我们手中并没有历史进步的遥控器。
疫情反思
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和防治,几乎是说明莫兰复杂性理论的鲜活案例。 不同国家对突发疫情共同的迟钝、忽视、盲目和掉以轻心,各种手忙脚乱、应对无策,凸显的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困境。只能说人类是健忘的,我们太习惯了理性的、线性的、严格规划的、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,沉浸在“岁月静好”的秩序感中,而对潜伏在身边的随机、突发的风险缺乏敏感和准备,也缺乏与病毒长期共生并存的生存智慧和技巧。许多人在预言全球化进程的终结。当世界陷入隔离、分裂、各行其是的混乱之时,只有无国籍无护照的病毒在继续全球化进程。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,许多主观的、刚性的、静态的、曾经有效的管理失效了,陈旧的治理框架在动摇,有人发推文说“听到了梁柱噼啪作响的断裂声”。
政府处置的快速高效和顾此失彼,凸显了行政化的优势,也暴露了其功能割裂、信息不畅等固有弊端。因为大国疫情的防治,是高度综合复杂的问题:既包括防疫、隔离、救治、疫苗研发等医疗和公共卫生事务,需要整体性、专业性的社会动员和管控;也需要对经济活动、劳动就业、学校教育、居民日常生活、弱势群体救助等作出安排;需要有效的社会参与、基层的社区服务,需要充分的信息流通、报警、表达和宣泄的机制,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,国际合作和建设性的大国外交。在收治和医疗、“封城”的社会管理、资源供给和配置、信息控制等几个主要因素中,不同国家的不同模式,值得日后的深入总结和评价。

专家系统的公信力同样在被贬损之中。各说各话的专家意见,无法兑现的疫情预测,夹带私货的用药方案,往往令人摇头。医学研究虽然已深入到分子、基因的层面,在微观上应该说是极其科学化了;但医学研究的整体范式,仍然是分离的和割裂的。病患是一个个具体的人,其年龄、基础性疾病、身体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,治疗方案理应是各不相同的。分析的还是综合的、微观还是宏观、治病还是治人,正是中西医之争的一个文化背景。
在高度专业化-科学化的研究过程中,人的价值迷失并非夸张。只要想想走火入魔的“基因编辑婴儿”案(主犯贺筑奎已入刑),即可明白“纯粹的”科学研究在反人性上走得有多远。这也正是人工投放病毒之类“妖言”泛滥的一个背景——除了自媒体时代众声喧哗、蛊惑人心的言论、众多毁灭世界的阴谋论灾难片的影响;也是由于公众对科学的伦理、科学家的信任感降到了某个低点。
至于“民主的退化”,只要想一想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,那么多致力于恶化大国关系、喊打喊杀的“战狼式”言论,对温和理性的方方的深仇大恨,就令人有不知今夕之感。人们在思考为什么尽享改革开放的好处、并无文革经验的一代,会变得如此偏狭极端,暴戾乖张?他们不惜一战的叫嚣,有对于民族命运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理性考量吗?他们对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最丑恶、破坏最为惨烈的灾难,有真实的感觉吗?
有人提出“思想病毒”的问题,在这次疫情中,其危害并不比生物病毒更小。众多微信群同学反目、亲友冲突,反映的是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撕裂。当然有教育的原因,这主要是来自社会生活和舆论环境的“大教育”。在信息-知识-智慧的教育逻辑中,许多狂热的头脑仅仅是被定向的信息所左右。所以有这样的金句“互联网让聪明的人越来越聪明,愚昧的越来越愚昧,完全取决于你从网上看到的是什么,以及你能看到什么。”绝大多数网民根本就没有见识过推特和脸书(民间甚至有推特就是“推翻特朗普”的笑话),却照样理直气壮地隔空叫骂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则迷失在碎片化的知识中,失去了“把知识加以背景化和把它们加以整合的自然的禀赋”。
一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对阴谋论照样深信不疑,无疑是教育的悲剧。但这种整合思维的能力又不完全是教育出来的,莫兰称这种禀赋具有某种天然性,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常识”的力量。 是非善恶的观念、正确的选择和判断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“常识”的背景所决定的。这一背景不仅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,更是包括人性,善良、诚实、内心的勇敢和自由之类基础性品质和经验所积累的。
教育何为
莫兰将教育的任务确定为“迎战不确定性”,因为“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。”
这需要教育改革与思想改革的互动:“教育的改革应当导致思想的改革,而思想的改革应当导致教育的改革。”他引用康德的话: 启蒙取决于教育,而教育取决于启蒙。这正是我们在现实的改革中一再遭遇的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困境,本身就是“不确定性”的一种体现。
哲学家的方案并非现成的标准答案,因为“一个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的土地,而是获得新的目光”。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,莫兰提出了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,但他将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归纳为“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”,这是针对“充满知识”的头脑而言的。它包括提出和处理问题的一般能力,“明智地思维”以及质疑的精神;其次是连接知识的能力,即是“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”,从而形成“恰切的认识”。这种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,是“迎战不确定性”最主要的能力,是对教育的“绝对要求!”
这是一种将教育过程“生态化”的思维:将事件、信息、知识放置在其特定的文化的、经济在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自然环境的联系之中,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的思考,对整体问题也必须进行局部的思考。从小学开始就把对人类地位的探询和对世界的探询连接起来。在教学过程中要超越“原因-结果”的线性因果性,认识相互关联的因果性、循环的因果性,以及因果性的不确定性,形成对复杂性的认识。国内中小学创新教育的探索,开展的主题式、项目式的跨学科学习,正是这样的实践。我们已经在重视知识的连接,需要在思维层面对线性因果关系的质疑和超越。

莫兰对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教育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。在小学阶段,把孩子刚刚觉醒的意识所具有的自然的好奇心,引向最初的探询:什么是人类、生命、社会、世界、真理?可以从原人进化的探险立场出发,提供生物-人类学的结合的课程。而中学是学习真正成为文化的东西的场所,要建立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对话,任何专业的教育最后都应引入哲学,对合理性问题进行探究。
我特别感兴趣的两点,一是莫兰特别强调在中学教育中, “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不是被牺牲,而是被提升。中学教育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人文文化。”因为包括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艺术等等的人文文化是一种“总体文化”,它承载蕴涵的是一种“人类精神应用于各种特殊场合的一般智能。”他主张“应该恢复文学完全的权能,”而历史学应该起一个关键作用。莫兰是把人文文化视为沟通、交流和连接各种知识、理念、信仰的桥梁和粘合剂,超越因隔阂、割裂而造成的各种狭隘、盲目、浅薄和偏见,从而涵养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解和同情关怀、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。因为“在任何文学的、电影的、诗歌的、音乐的、绘画的或雕塑的伟大作品中,都存在着关于人类地位的深刻的思想,” 艺术则教会我们更善于以审美的方式看世界。
例如,“小说以及电影向我们提供了在人类科学中看不见的东西,即人类科学遮蔽或消解的人类存在的生存的、主观的、情感的特点,人类一直经验着它的热情、它的眷爱、它的憎恨、他的允诺、他的梦想、他的幸福、他的不幸、遭遇着幸运、厄运、欺骗、背叛、偶然性、命运、宿命……”所以,疫情中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,如果把更多地读小说、看世界经典的优秀电影作为重要内容,可能比上网课有益得多。
其次是我们所说的“媒体教育”。外在于学校的传媒文化通常被知识界所鄙视并不予理睬;然而,它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可能比学校更为强大。莫兰呼吁学校教育不应该自我封闭,“如同在传媒文化汹涌澎湃的形势下被围困的城堡。”因为教育者需要通过流行文化去认知我们这个时代的“时代精神”,也即青少年的文化特征;同时,需要“理解多种形态的文化的产业化和超级商业化的过程。”这应当成为教师要进修的一课,是一种必要的社会认知。例如在小学就帮助学生认识影像处理和编辑对真实性的改变,以及对电视节目和网络游戏进行评论。
还是需要回应教育改革与思想改革的互动关系。在现实中,这一问题转化为“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究竟如何起步?”莫兰认为“中小学教师将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,”他们首先要走出被外部世界围困的“教室的城堡”,首先在他们的思想中引入探求总体性问题、复杂性问题的视域。但是,“谁来教育教育者?”这也正是我们在国内的创新教育实践中深感困惑的。莫兰的答案,这将是少数受到鼓舞、已经具有使命感的教育者,通过少数先行者来影响和带领更多的人。因为“创举总是来自少数人”,而改革的起步“只能是违反常规的和遭受轻视的。”
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解,就是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。在混沌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化中,来自个体的自发性、自主性和“自组织”,成为构建新秩序的重要机制。以莫兰此书的献辞作为本文的结语,是再恰当不过的了:
“我尤其寄希望于被教育者,当他们有幸看到此书时如果正值教育令他们感到厌倦、沮丧、被压垮或绝望之际,他们可以利用本书的提示把他们的自我教育掌握在手中。”

本文作者:杨东平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
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
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

